易水寒(七)
秋初。风还是热,夏天仿佛被捆绑在山上、树上、房顶上,除了早晚天气稍有一丝凉气。
七夕。这日子在安舟村,或许还有姑娘们会对着月亮穿针乞巧。在这县城,在这镖局,只有铁锈味和汗酸气,还有账本上抹不平的红痕。
苏超把我叫到账房,扔给我一套半旧的青布镖师服,肩上绣着暗淡的“清风”二字。“换上。跟你越哥和七姐走趟小镖。”
莫小七生的风摆杨柳,据说是苏超远房亲戚,家里遇事,从江南来投。本想让她去长安书院读书,当然是以读书为名,更希望的是能结识到才子书生或富家子弟,了了终身大事。
偏生小七不是个安生的主,不喜欢读书,倒是愿舞刀弄枪,苏超无奈,也教他些功夫,以作防身。这次听说去忘忧谷,吵吵闹闹,一定要跟上。任务简单,路程不远,苏超就随了她的愿。
君子越人如其名,话不多,腰杆总是挺直的。虽是镖手,却喜欢白衣,使一柄细长的剑,有翩翩公子风。
任务真是简单得出奇:送河东商帮那位刚接手不久的少掌柜狂流,在七夕之前去到城西三十里的忘忧谷。
狂流,年纪不大,二十出头,锦衣华服,却掩不住眉眼间的焦灼和多年的放浪形骸淘空了的苍白。他怀里紧紧抱着一个紫檀木长盒,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
“七夕……忘忧谷……”狂流喃喃自语,眼神发直,“她说在那里等我……一定要到……”
没人问“她”是谁。干镖局的,第一要紧的不是功夫,是闭上嘴,蒙上眼,只走路。
莫小七牵来三匹马,外加一辆单乘的简陋马车给狂流。马依旧是那几匹瘦马,喷着响鼻,不耐地刨着蹄子。
“易水,你押后。”君子越翻身上马,动作干净利落。他的声音平稳,却自带一股令人信服的气度。
莫小七冲我挤挤眼,丢过来一个水囊:“小子,第一次走镖,别慌。眼放亮,腿夹紧,跟着跑就是了。”水囊里是辛辣的劣酒,灌下去,一条火线从喉咙烧到胃里。
城西的路越发荒凉。初升的上弦月惨白,照得路面像蒙了一层霜。两旁的树木张牙舞爪,投下幢幢鬼影。忘忧谷,这名字听着就透着一股神秘的静谧。
狂流坐在马车里,不住地催促,声音尖利:“快!再快些!误了时辰,我剥你们的皮!”
莫小七嗤笑一声,低声道:“赶着去投胎么?”
君子越眉头微蹙,警惕地扫视着四周越来越浓的黑暗。他的手,一直轻轻搭在剑柄上。
我握紧了苏超给的那把短剑。冰冷的触感让我保持清醒。《七种兵器》里的字句莫名在脑中翻腾:最可怕的不是已知的险恶,而是未知的等待。


 鲜花(
鲜花( 鸡蛋(
鸡蛋( 发表于 2025-8-22 17:11
发表于 2025-8-22 1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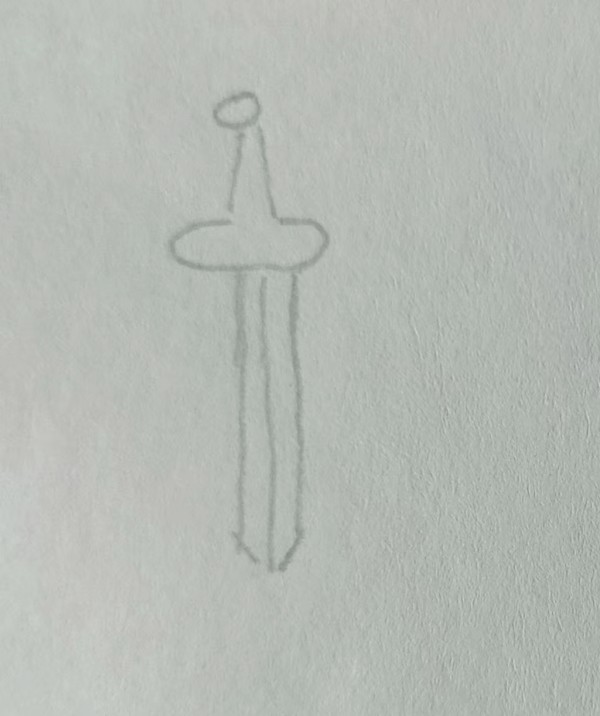
 好运卡
好运卡
 楼主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