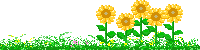过年抽出时间陪爸妈去了趟三里屯儿,是初五的事儿。原本只是随口的一个提议,因为平日里那里最是堵车,想乘着过年城里人少的空挡去转转。没想到我妈却认真起来,翻出衣柜里她觉得合体的服装,在镜子前比划了许久。我心里暗笑她的隆重,不过是个商业区罢了,又不是去赴什么要紧的宴会。
爸开车,我和妈坐在后排。车子距离太古里还有百十米就走不动了,妈说去对面三里屯SOHO停车场,绕过车流往前开才发现原来太古里地下停车场爆满,所以排起了长龙。还是妈轻车熟路,我不免赞了一句,只见她眼睛看着车窗外,像要把那些飞快后退的楼影都认一遍似的。我这才意识到,对她而言,这确是一场赴宴:赴一场与旧日时光的约。
从停车场上来,迎面便是对面太古里那片错落的玻璃幕墙,在冬日的薄阳下,泛着冷冷的,却又亮得晃眼的光。过马路的游人早已织成了河,年轻的男女,举着手机,举着奶茶,穿着时尚的服装,脸上是饱满的笑容,像这节日的空气般很甜。过街的人群更是一道壮观的风景,绿灯一亮,黑压压地漫过来,淹没了斑马线,又漫向另一片光鲜的街区。我妈站在人潮的边缘,忽然有些怔住了。好似极力地想从这片光洁的,现代的,略显得喧嚣的玻璃与钢铁之间,寻出一点旧时的痕迹来。可那些痕迹,大约是太难找了。
三里屯儿承载了妈妈整个儿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她开始指给我看:这儿,这儿从前是个饭店;那里,那里是个洗澡堂,每到过年洗澡都得排大队。后来改革开放,这里变成了酒吧一条街,再后来,建成了现在的太古里行业街区。
妈指着三里屯SOHO那些高楼大夏说:那里曾经是一大片三层楼的房子。看那里,那个位置是小学和中学。妈妈带着回忆说:看那儿是副食店和粮食店,买豆腐和白薯都要排一夜的队;过年的时候,按定量供应花生和瓜子,队伍也排的老长。
我听着,眼前的景象便也恍惚起来。那喧闹的,透明的商业街,仿佛像一张单薄的,崭新的画儿,被她的话语一戳,便隐隐透出底下另一张画来:灰蒙蒙的,却有厚度的,带着煤烟与熟食气味儿的,属于她的,也属于一座城的旧梦。
妈指着下沉式广场说:这是楼前的一个大空场,我们就在这儿踢毽子,跳皮筋儿,捉迷藏......,她的眼睛亮了一下,像真的看见了那些奔跑的影子,那些遗落在楼群里脆生生的笑声。
我们慢慢地走着,从太古里逛到SOHO。她讲她的学生时代,讲清晨约上小伙伴儿一起去上学,讲着邻居大娘一家对他们的照顾。她说得很碎,东一句,西一句,像在拾捡一地零落的珠子。我只静静地听,不敢打断,怕一出声,那根细细的,串起珠子的线,便会断了。
忽然,她不讲了。我侧脸看她,人流在我们身边涌过,像一条喧哗的河。她的目光,投向远处那片光鲜的,年轻的笑脸,却又像穿透了它们,看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她的眼角,分明有一点亮晶晶的东西,在午后的光线里,极快地一闪。
平时我最懒得听我妈讲述的回忆,但是今天在这个繁华的街区,听着妈妈的讲述,我知道,妈妈眼中那一点泪光里,装着的,是她整个儿的,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回去的车上,她靠在椅背上,久久地没有说话。窗外,太古里的灯火渐渐汇成一片模糊的光海。我知道,那里还有她对姥姥姥爷的回忆,我忽然明白,今天我陪她走的,是一条怎样的路。这条路,于她,是密密缝进生命里的一段锦,织着她全部的学生时代,她的悲欢,她的来处。
我心里暗暗想着,我有空一定好好听听妈妈的回忆,我要写出他们那个时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