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x
本帖最后由 哑弦 于 2017-12-27 22:13 编辑
绒花犹在,芳华已逝
文/哑弦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那是1976年,某军区文工团的“活雷锋”刘峰从北京接来了舞蹈新兵何小萍,自幼缺少家庭关爱的小萍在新集体里依然被当做笑话。为了让进牛棚的父亲早日看到自己穿军装的样子,她偷偷拿了同舍林丁丁的军装去拍照,被发现后斥之为小偷;有人爱美将海绵缝在内衣上被人讥笑,所有人都认定只有她能干得出来;因为来自农村,被合作的男演员嫌弃“出的汗都是泔的”,而只能去服装组打杂;好不容易有个跳A角的机会,却因为愤怒刘峰命运的不公,装病被踢出了文工团,分派到野战医院做了一名护士。
“阶级”这个词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从古自今却在中国的土地上演绎得最为直白露骨。到如今这个年代,还时常能听得某些人口中念叨着所谓的精英圈层,大抵也是阶级理论的翻版。而何小萍,不过是万千底层人物的一个缩影。就算凭着天分、努力,幸运踏入了一个往日里需得仰望的世界,这个新世界也不会那么容易接纳你。千般挑剔,万分磨折,秉持初心的人注定会因难以融合而饱尝痛苦。
而我们的男主角刘峰,是文工团里最老实质朴的人,不仅日常里包揽了团里大大小小的脏活累活,遇到危险难题也是当仁不让,对所有人关怀备至,也让所有人在习惯了他付出的同时,无视他作为人的基本感受——每一个人,无论高低贵贱,心里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份情感。命运的转折是从他对林丁丁的表白开始的,一向隐忍的他拥抱了心底喜欢的女神,没想被人看到,于是被女神质疑告发,当做耍流氓处置下了基层连队。
人生的某些运数仿佛就是这样。在大众眼里,神是无知觉无个性不被质疑的存在,被捧上神坛的人必须以神的要求来要求自己,有意也罢,无意也罢。所以穗子说:后来我明白林丁丁当时的想法了,她觉得有种英雄被亵渎的感觉。刘峰没有错,他不过是坦白了内心的情感。听到这句旁白的时候,你甚至觉得林丁丁也没有错。精神偶像的坍塌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女孩陷入桃色事件,在那个不允许有个人意志活在他人眼光中的荒唐年代,似乎只能以告发对方来保护自己。人性的薄凉,是悲哀,也是无奈。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也许是故事发生在文革的尾声,也许是广电局审片的需要,男女主人公虽然时运不济,我们却没有在影片中看到曾听闻的属于那个年代的更多更残酷的细节。70年代末,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刘峰上了战场,英勇地丢了一支胳膊;何小萍跟随野战医院上前线救死护伤,一直战斗在第一线。战争结束,两个人都成了英雄,何小萍却因强烈的现实反差和战争阴影造成精神崩溃。
虽然没有亲历过战争的残酷,看过那么多影片,也知道战争带给人的心理创伤是何等深切。眼看着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血肉之躯被枪炮摧毁湮灭,血腥到面目全非,那种深刻巨大的恐惧、紧张、抑郁和无力感也许会伴随一生都无法根除。编剧对何小萍不算残忍到底,她在观看了文工团的慰问演出之后竟然自愈了。很喜欢那段独舞的镜头,广袤的夜空下,月色清冽,整个天地都是舞台,小萍身着病号服,眉眼带笑,舞得那样忘我而投入,仿佛那些黑暗过往从来不曾降临......
善良的人总是大抵相似,且互相懂得。刘峰也依然是刘峰,拖着残疾的身躯默默地活在都市的最底层,哪怕被人歧视刁难。若干年后,他们重逢,他用那只假手轻轻拢住她,一如当年给予的关怀温暖。穗子说,多年后的文工团聚会,许多人都或多或少带着被岁月磨出的憔悴疲惫,唯有刘峰和小萍,最是淡然知足。也许,要感谢时代的变迁,感谢精神自由时代的到来,让生活给予了善良的人们最大的福报。
这就是《芳华》。应该承认,冯小刚依然算得是国内有良心且真性情的导演之一。有人说,冯小刚在《芳华》中要做的事是分析那一代人未曾出口的潜意识。虽然我觉得影片还做得不够,论不上多深刻,与国外许多优秀影片相比,人物的性格设定还流于剧情的摆设,主题也尚未做到完全由剧中人来自然引渡,剪辑也颇多碎片,但敢于以尽可能的诚意关注人性本身,探讨时代与人的命运关联,这份勇气,已然值得致敬。
电影结束的时候,韩红的《绒花》响起来,空灵清曼,令人沉醉,我的眼前却浮现出刘峰在战争过后回到文工团排演大厅幻想的那一幕——那是影片里最美的场景,也是他们那代人挥洒青春的最后影像。《绒花》曾经是电影《小花》的插曲,如今,又一次在《芳华》里诠释着青春的美丽。歌声中,那些个沉郁悲凉的时代,那一群人最好的芳华,已随流水逝去,只留下一行渐行渐远日益模糊的脚印,任人凭吊、感伤、质疑或者沉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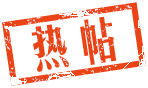


 狗仔卡
狗仔卡
 鲜花(
鲜花( 鸡蛋(
鸡蛋( 发表于 2017-12-27 22:13
发表于 2017-12-27 22:13

 提升卡
提升卡 沉默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变色卡 抢沙发
抢沙发 显身卡
显身卡 楼主
楼主






